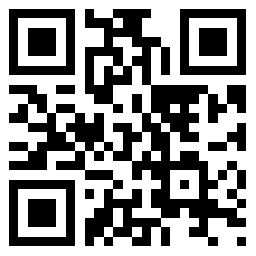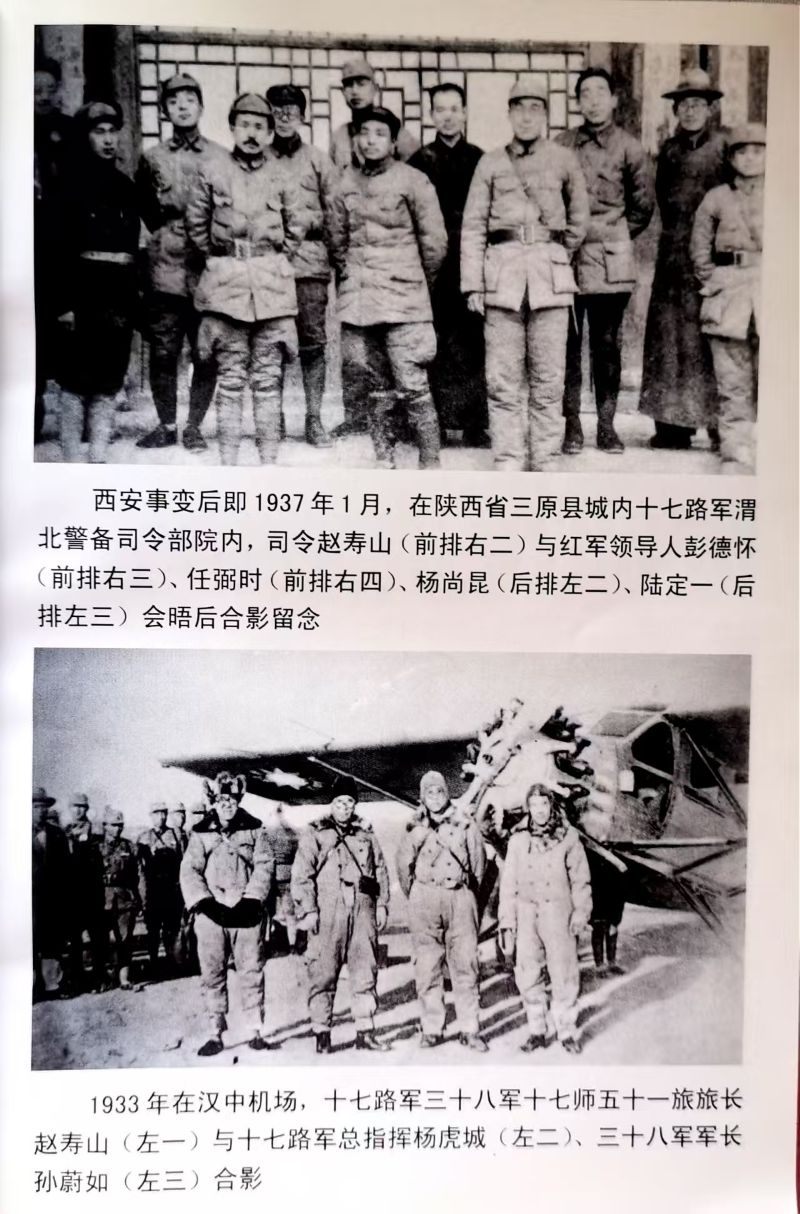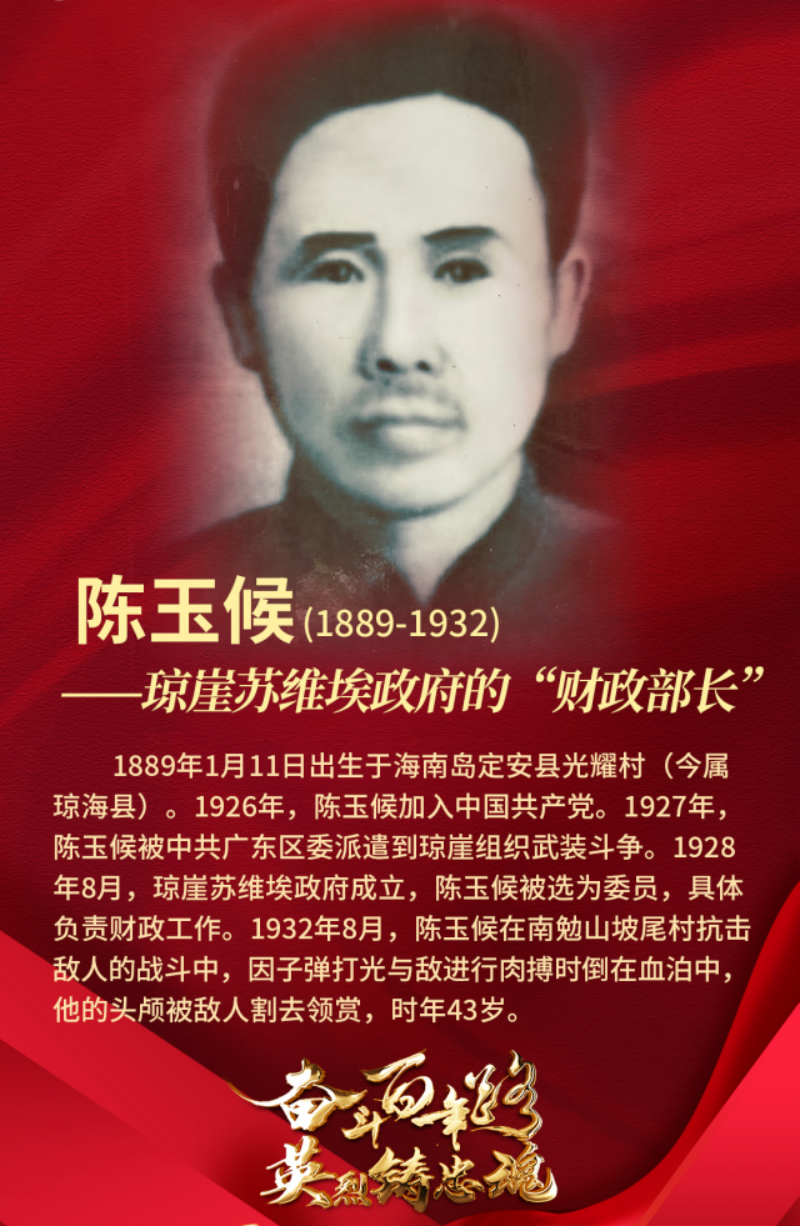(作者:符永涛)在中国古代边疆开发的长卷中,海南岛因远悬南海,长期被视作“化外之地”,早期人物事迹多隐没于史海。直至盛唐,崖州(今海南)人何履光以卓著军功与治政才干跻身朝廷高阶,成为海南史上首位有明确记载的朝廷高官。其生平虽散见于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《资治通鉴》及唐人笔记,如散落的拼图,却清晰勾勒出盛唐边疆治理与民族交融的生动图景。
一、家世渊源与入仕路径:崖州沃土育英才
何履光的籍贯,唐人戴孚《广异记》载之甚明:“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,朱崖人也。所居傍大海。”朱崖即隋珠崖郡,治所在舍城县(今琼山旧州镇);唐高祖武德五年(622年),珠崖郡改置崖州,治所未变,故学界多推断其家族世居于此。

从唐代崖州社会结构观之,当地居民含黎族先民与中原移民。考其族属,“何”为典型汉姓,而彼时黎族尚未形成汉式姓氏体系——男性多称“帕+名”,女性称“拍+名”,直至唐后期才渐借汉姓,明清推行户籍制度后,或音译氏族名、图腾为姓,或由朝廷赐姓。由此可证,何履光非黎族后裔。然《海南何姓族谱》未将其列为渡琼始祖,仅载南宋何兴、何仁德二人,推测其家族迁居海南早于二者,未入记载或因后世影响力有限,或因修谱时史料散佚。结合崖州历史背景,其家族更可能是较早迁居的汉族官吏后裔——或为冼夫人(逝于旧州镇)麾下留驻部众的后代,或为崖州衙门僚属之家,这为他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创造了条件,使其得以从珠崖沃土中脱颖而出。
唐代选官以科举、门荫、军功为要途,何履光的仕途更偏向“军功举荐”。崖州虽偏远,却是岭南与南海贸易的关键节点,朝廷驻兵防备海盗、安抚黎族。开元年间,崖州“峒蛮相聚为乱,掠商旅”,史载何履光“少习骑射,晓岭南地理”,青年时或服役于崖州军镇,曾率乡兵协助官军“焚其巢穴,抚其降者”,因平定黎族部落冲突崭露头角,被举荐担任官军要职,此为其仕途之始。
二、宦海浮沉:从边郡将官到封疆大吏
何履光的仕途巅峰在唐玄宗、唐肃宗两朝,历任都督、特进(文散官第二阶)、左武卫大将军(禁军高阶)、岭南节度使等职,终官正二品,为唐代海南籍官员中职位最高者。其履历与天宝年间唐南战争、安史之乱等重大事件深度交织,堪称当时折冲扞难之臣、岭南重臣。
(一)治理崖州:首位本土出身的地方长官
史料明确其曾任都督,未载任职地点。结合籍贯、早期经历及唐代官员晋升逻辑推断:何履光后期官至岭南节度使、左武卫大将军,必经地方中高级职务历练;崖州为其故乡,又是边疆治理要地,由熟悉当地的本土官员任都督,契合“以边治边”行政逻辑;且他早年因军功已在军方任要职,晋升为辖区最高军政长官“都督”,亦合唐代晋升路径。故可推断,何履光曾任崖州都督,成为海南史上首位由本土人士担任的最高军政长官。

海南民间相传,何履光任崖州都督时,推行“恩威并施”之策:对黎族“奥雅”(首领),“赐以锦袍、银带,约以互不侵扰”,如与琼山、文昌、定安诸首领“歃血为盟,约定和谐共生”;同时传授耕织技艺,引导其从游牧转向定居农业,分配农具、种子助力生产,进而稳定治安、改善民生,这些传说与其履历恰相印证。
民间另有说法,他任内主持修整岛内古道,升级崖州与大陆的陆海通道,使崖州沉香、吉贝(棉花)、海货及诸蕃珍宝的贸易量显著增长。这些举措稳固了海南岛的统治秩序,为其发展与繁荣筑牢根基。
(二)南征南诏:立铜柱宣示主权
天宝年间,唐朝与南诏(今云南)关系恶化,南诏、吐蕃成西南边疆大患。何履光全程参与“唐南战争”,可考军事行动凡三次,首次出征斩获卓著:
1. 收复安宁及立铜柱宣主权:天宝八载(749年)十月,唐玄宗命特进何履光统率十道兵自安南北上征讨南诏。此次出兵早于鲜于仲通伐南诏,目标直指控制盐利的安宁城(今云南安宁)——当地五盐井“岁得盐数十万斛,以资军用”,为南诏经济支柱。何履光率军成功夺取安宁城及盐井,使南诏“国用大蹙”,并仿东汉马援故事复立马援铜柱宣示主权,而后还师,此为唐代经营西南的标志性事件。
2. 后续两次征讨失利:天宝十二载(753年),何履光以左武卫大将军身份率岭南五府兵再击南诏,此前姚州都督贾颧所部已全军覆没,他最终仅以身免;天宝十三载(754年),时任广府节度使的他随李宓率十道兵再征,唐军水陆并进却遭南诏与吐蕃联军夹击,因“瘴疠大发”且无防备而溃败,李宓沉江而死,何履光收残兵撤离。虽后两次失利,其军事行动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南诏扩张。
(三)勤王平乱:安史之乱中的忠勇
天宝十四载(755年),“安史之乱”爆发,叛军迅速占领洛阳、长安。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,急召各地将领勤王。时任岭南节度使的何履光接诏后,即刻调发广州、桂州兵万人溯湘江赴南阳驰援,途中与叛军将领武令珣交战,斩将三员,夺粮船百艘,暂通粮道。虽因兵力单薄未抵灵武,却尽显忠勇担当。
至德元年(756年),肃宗命贺兰进明接替其岭南节度使职,何履光改任左武卫大将军,统禁军驻守凤翔。关于其结局,史料记载不一:一说此后无载,推测病逝于任;另有记载称其最终归隐广西贵县。
三、史料缺憾与历史评价:被遗忘的边疆干才
何履光未入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列传,仅散见于他人传记及事件记载,此与安史之乱后史料散佚相关——战乱中多地档案损毁,诸多官员事迹未能留存。尽管史料零散,同时代评价却颇高:时人赞其“有谋赞之能,明恤之量”,兼具谋划之才与体恤军民之度;《册府元龟》载,肃宗曾称其“虽起自遐裔,忠节著于本朝”,明确认可其边疆出身与忠君之心。
作为海南史上首位跻身朝廷高阶的人物,何履光的意义远超个人仕途:他的出现,标志着海南岛经数百年开发,已能培育参与全国军政事务的人才,打破“蛮荒无才”之偏见;其南征南诏时“立铜柱宣疆”之举,成为古代王朝维护边疆主权的象征;任岭南职期间的区域治理实践,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。
琼山旧州镇至今流传着他凿井引水、传授农耕、设义学推动汉黎交融的传说,这些传说凝结着百姓对其兴农启智、促进民族融合的集体记忆。这位从崖州走出的边疆将领,虽未留下详尽传记,却以“宣疆勤王”之功,在海南开发史与唐代边疆史上写下不可替代的一笔——他用自身经历证明:边疆从来不是历史的“边缘”,而是孕育英才、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舞台。
【编辑:庄观伟】